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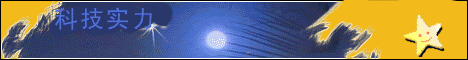
![]()
 |
|
|
|
|
石破天惊:揭秘遗传学千古奇案
摘要
孟德尔设定的基因定义被误解导致了罕见的100年来遗传学千古奇案的形成。其致命点是把一个控制个体规格的模板遗传要素供奉为遗传物质的全成分也即个体的制造者。当科学揭示基因(DNA)在个体制造过程中不耗能不做功不建立3’、5’-磷酸二酯键时这个所谓的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就成为了反科学的永动机(能创造化学能使核苷酸、氨基酸等原料转变成个体及其性状等产品。能量守恒定律被推翻)了。本文细述了误解的产生及孟德尔实验的真实意义,最后讨论了导致误解产生的深层原因。
1.导言
2010年文特尔团队报告他们合成了一个人造基因组并宣称用它制造了合成生命[1]。这表明基因(组)是个体(细胞)的制造者。这与“种质:生殖细胞的遗传物质:基因”[2]这一“现代遗传学”共识是一致的 [100年来类似的话太多了:摩尔根(T. H. Morgan)说“只要有一个整组的单元,就有可能具备产生新个体的能力”(见卢惠霖译,基因论,1959年科学出版社版:第20页或Morgan, T.H. (1928) The Theory of the G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pp28);我国著名遗传学家、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主席赵寿元教授也说“假如通过人工合成最小基因组DNA,再加一些生命活动所需的其他组分,如水、金属离子、有机分子等,能够构建出生命体”(赵寿元,最小基因组研究进展,生命科学2001;13(1):23-27)。他只是传达了“现代遗传学”界的共识,绝不是他个人的创见]。
但是国际知名生命科学家,美国加州Scripps研究所的杰拉尔特·乔伊斯博士,在《纽约时报》报道的回应人们惊呼合成细胞是一个新的生命形式或人造细胞时,说:“当然,这是不正确的,其祖先是一种生命形式”。纽约时报继续写道“文特尔博士拷贝了一种细菌的DNA,并将其插入另一种细菌中。第二个细菌制造了这个所谓‘合成细胞’的所有蛋白质和细胞器”[3]。这种说法表明基因组并不是个体(包括细胞)的制造者[我国学者方舟子2010年6月2日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人造生命”诞生了吗?》中也质疑说“不能说照葫芦画瓢地抄了一张设计图,就相当于制造出了机器”]。
上述两者的对立暴露了“现代遗传学”的危机。两者是针锋相对的,只可能有一个是对的。为了鉴定真伪我们只能回到孟德尔那里去,毕竟基因定义(最原初所指)的设定者是孟德尔。
2.超低级错误致孟德尔基因定义被误解100年
为了解答实验中出现的疑问孟德尔提出如下基因假设:(英语)“ If the tall variety contains in its germ cells something that makes the plants tall, and if the short variety carries something in its germ cells that makes the plants short, the hybrid contains both; and since the hybrid is tall it is evident that when both are brought together the tall dominates the short, or, conversely, short is recessive to tall” [4]。中国卢惠霖教授的中文译文:“如果高株品种的生殖细胞含促成高株的某种东西,而矮株品种的生殖细胞含促成矮株的某种东西,那么,杂种便应该具备这两种东西。现在杂种既然是高株,由此可知两种东西会合时高者是显性,而矮者是隐性”[5]。文中的某种东西(英语something)就是后来所谓的“基因”[参考几个例句或许能加强对这段文字特别对“make”应用的理解。如"The aircraft factory contains drawing that makes the aircraft big, and also contains drawing that makes the aircraft small".(译文为“飞机厂有促成大飞机的图纸,也有促成小飞机的图纸”);" The casting factory contains mould that makes the head of the product arrow-shape , but also contains mould that makes the head spherical".(译文为“铸件厂有促成产品头部为箭头型的模具,也有促成头部为球形的模具”);"The decoration company contains design scheme that makes my house European style, or Island style".(译文为“装修公司有促使我居所为欧式风范或海岛风范的设计方案”]。
文字记录证明:基因是促成个体及其性状吻合某特定规格(而不是别的任何规格)的产品规格信息要素(这类信息可以用文字、数字、几何、物理或化学形式负载在模板、图纸、模具、设计书等载体上。例如只有在模板引导下,制造者的操作要素才能制出与模板规格吻合的产品)。基因并没有个体及其性状之制造者的含义。
可见,称基因(DNA)为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认为它能制造个体完全是100年来人们把“make”错误理解为“produce”的恶果。
孟德尔论文已属历史文献,其对基因之规定已成历史铁证。任何德语原文、英语(译文)、中文(译文)或世上其它语言(译文)的专家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重读、重新翻译该段文字。但要更改孟德尔的基因定义怕是不可能的了。[基因定义的确定性不仅依赖于定义原文的词义及语法结构,更依赖孟德尔实验本身的支撑。任何问题及其答案都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孟德尔实验提出的问题与孟德尔基因定义的假设符合正确的逻辑适配。这才是基因定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因。]
3.事实对基因定义的核实
1944年艾弗里团队确认基因由DNA组成时指出:“DNA能刺激无荚膜的RII型肺炎球菌制造出荚膜来”[6](英语:“DNA is capable of stimulating unencapsulated R variants of Pneumococcus Type II to produce a capsular polysaccharide”[6].)。这与孟德尔的基因定义完全吻合,也即基因(DNA)是制造特定性状的产品规格信息而不是制造者。
后来分子生物学取得的成就更为上述事实提供了全面充分的事实证据:一方面DNA不可能是个体的制造者,因为在个体形成过程中它不耗能、不做功,不建立3’、5’-磷酸二酯键或肽键;另一方面DNA直接是RNA的模板,间接是蛋白质的模板,故而是制造个体及其性状的模板源。这些知识如今都已属教科书或百科全书上的常识。
在以上事实面前,文特尔宣称DNA制造了“人造细胞”实际上已经成为证明“现代遗传学”荒诞的样本。事实是:由文特尔团队合成的基因组(DNA)若制造了“合成生命”,那么DNA就成为永动机了。这是反科学的。因为它意味着DNA不耗能不做功就创造了化学能使含低化学能的核苷酸、氨基酸等原料转变成含高化学能的个体及其性状。这与能量守恒定律相悖。
4.孟德尔基因定义的第二个提示
孟德尔基因假设中明显提示生殖细胞内还含有第二个制造要素。因为基因只是使植株(plant)为高(tall)的促使者,这意味着必定存在着一个接受基因促使而制造高或矮植株的要素(若没有它基因去促使谁?高或矮的植株又怎么能被制造出来?),或者说存在一个需由基因导引才能制造出符合基因限定规格植株的制造要素。这正如飞机厂制造出飞机还应该有一个能按图纸指示制造飞机的生产线,铸件厂应有按模具制造头部为箭头型铸件的浇注工或浇注机,装修公司应有按设计方案实施装修操作的工人及工具。在受精卵里按基因模板实施性状乃至个体制造的就是卵转录酶系[7]。
艾弗里团队的宣称同样核实了孟德尔的这一提示。“DNA能刺激无荚膜的RII型肺炎球菌制造出荚膜来”(英语:“DNA is capable of stimulating unencapsulated R variants of Pneumococcus Type II to produce a capsular polysaccharide”)这句话清楚地提示RII肺炎球菌含有能按荚膜DNA导引制造出荚膜的操作制造力要素)。
由此可见,孟德尔的基因假设不仅言中了模板基因的存在,而且提示了性状(乃至个体)制造第二个要素制造操作者的存在。正确地提示了个体制造者由两个要素构成:模板要素及能按模板进行制造的制造力要素。
5.结论
100年来以基因(DNA)为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的所谓的“现代遗传学”是历史性误解产物。
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含两要素:生物个体的模板(基因或DNA)及能按模板实施制造操作的制造力(卵转录酶系[7])。
孟德尔的功绩是伟大的。他不仅发现了基因及其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生物中的遗传规律而且暗示遗传物质有两大要素:模板及制造力。
6.讨论
对孟德尔的误解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6.1 对遗传学两个基本问题缺乏认识,以致文不对题把“第二问题”的答案当作了“第一问题”的答案[8]。“第一问题”是遗传学最基本的问题。历史上预成论、达尔文的泛生论及魏斯曼的“种-质(Germ-plasm)论”试图解答的都是该问题。它问“谁制造个体(含性状)”?或“哪些物质制造了个体(含性状)”?孟德尔(实验)没有探讨“第一问题”。孟德尔实验提出的是为什么(豌豆的)“高株品种同矮株品种杂交的子代杂种即F1,都是高株”……?之类的问题[4]。这是问“谁制造个体(含性状)”吗?当然不是。这归属于“第二问题”。常见的“第二问题”问话有:“为什么高个子汤姆与他矮个子妻子的子女全是高个子”?“为什么汤姆儿子(或女儿)的鼻子像父亲的而耳朵像母亲的”?“为什么哈布斯堡家族的鼻子似乎是按一个模具塑造出来的”?……“第二问题”通常在两性繁殖的生物中显现。由于有(父、母)两个亲体,所以对制造者来说有了新问题:双亲中哪个规格模式会在产生的后代身上表现出来呢?规格模式的选择有什么规律呢?它问种质“什么东西促使你制造出父(或母)版或折衷版的个体(性状)的?” 孟德尔找到的正是“第二问题”的答案:亲体的规格模式遗传要素是基因,它按两条孟德尔定律遗传给子代。
6.2 遗传物质一元性是人类的惯性思想。从“预成论”的微缩小人到达尔文泛生论中的芽体以及魏斯曼的“种-质”,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历来被认为是一元的,没人提出过二元的遗传理论。因此,孟德尔找到一个遗传要素(基因)的事实被确认后人们就容易鲁莽地认为基因就是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特别是在人们对遗传学两个基本问题还缺乏认识的时候。这就大致雷同与母系社会的人见到女子生下婴儿就认为女子是婴儿唯一制造者一样,人类总是在客观事实的教训下其思维才越来越变得细致、周到、缜密的。
6.3 人们对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是制造者的概念太糊涂。在本文中提到遗传物质时总是注明是(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这是为了避免误会:基因(DNA)事实上仍是遗传物质之一(模板要素),但它不是“现代遗传学”所说的遗传物质,“现代遗传学”所谓的遗传物质等同于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尽管“预成论”、泛生论、“种-质(Germ-plasm)论”等的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都指向了个体(含性状)的制造者,本文提到的摩尔根、赵寿元(他们实际也代表了所有的遗传学家)也都认为遗传物质是个体(含性状)的制造者,但事实却证明人们普遍地不把制造者视为遗传物质的根本要义。如果人们能把制造者视为鉴定遗传物质之根据的话,首先就不会把孟德尔基因定义中的“make”词义搞错,因为人们就会注意到高株(或矮株)的制造者不是基因,从而就不会把基因理解为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其次也不会在艾弗里团队指出“DNA is capable of stimulating unencapsulated R variants of Pneumococcus Type II to produce a capsular polysaccharide”后依然没有看出DNA不是制造者,故而也就不是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而只是遗传物质的一个(模板)要素或促使制成某规格产品的要素。它显然表明人们可以在基因不是制造者的情况下依然承认基因是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可见人们对遗传物质(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是个体(含性状)制造者的观念糊涂至极,在认定遗传物质的时候竟忘了它应该是制造者的本质特性。结果酿成自我矛盾的基因概念:它既是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f the germ cells,却又不是制造者。
在华生-克里克发表DNA分子模型的文章后人们几乎马上承认DNA是(自)复制物质。可是实际上不存在DNA是(自)复制物质的事实依据。难道仅仅由于华生-克里克在该文中说过:“我们不免注意到我们设想的碱基配对方式直接提示了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拷贝机制”("It has not escaped our notice that the base specific pairing we have postulatedly immediately suggests a possible copying mechanism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9]?今天的人们不是不知道制造DNA需要建立3’、5’-磷酸二酯键,但人们不认为不会建立该键的DNA就不是复制物质。这实在是无可药救的。这就如同人们明明知道负片必须要依靠人或机器执行拷贝操作才能从负片制得相片但依然坚持说“负片是自复制材料”一样。DNA及负片明明是具有易被复制机制的物质或材料却被说成是能自复制的物质或材料。把被动者说成是主动者。这是指鹿为马,还讲什么科学?连讲理的基础都没有。人们的思维完全被魔法所控制了。这魔法就是人们历经权威“现代遗传学”长达数十年的熏陶获得的思想桎梏。由于一贯无视能建立3’、5’-磷酸二酯键的制造力的价值人们竟连为什么负链RNA病毒的RNA-没有感染性这样简单而必然的事也变成了遗传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了(还得依靠D. Baltimore et al.做实验来告诉他们原因[10])。他们习惯了DNA病毒的DNA在宿主细胞的转录酶操作下建立3’、5’-磷酸二酯键产生RNA继而发动感染,他们认为转录酶是免费午餐,是上帝必须供给的。遇到RNA-它虽然也是基因,但它被转录时需要的是RNA复制酶;而细胞内是没有该酶的,于是就不能发动感染了。此时此事人们就不懂了:为什么上帝不发免费午餐?为什么基因会没有制造力?实际情况是:由于细胞没有RNA复制酶,RNA病毒要有感染力必须自带或自制RNA复制酶。权威理论对人们的禁锢作用实在惊人以致当今的“现代遗传学”家们都进入了无须飞机生产线他们手中的飞机图纸都能制造飞机的痴迷境界。
病毒RNA-没有感染性实际是自然界为人们敲响的一次警钟。可是人们并没有被这次警钟敲醒,人们依然没有警觉到细胞内转录酶与上述RNA复制酶是完全相同的角色。他们从来没有如下危机感:世界上若没有转录酶,所有细胞都不会出现。届时应该是“现代遗传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把永动机DNA请出来复制大量的DNA以及制造大量的RNA继而大量的蛋白质……世界还会有细胞吗?
References
[1] Gibson, D.G., Grass, J.I., Lartigue, C., Noskov, V.N., Chuang, R.Y., Algire, M.A., et al. (2010) Creation of a Bacterial Cell Controlled by a Chemically Synthesized Genome. Science, 329, 52-5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90719
[2] Germplasm.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germ%20plasm
[3] Wade, N. (2010) Researchers Say They Created a “Synthetic Cell”. New York Times,20 May 2010.
[4] Morgan, T.H. (1928) The Theory of the G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2.
[5] 摩尔根著。卢惠霖译。基因论。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
[6] Avery, O.T., MacLeod, C.M. and McCarty, M. (1944) Studies on the Chemical Na-ture of the Substance Inducing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Journal Experiment Medicine, 79, 137-158. https://doi.org/10.1084/jem.79.2.137
[7] Zhou, M.Y. (2018) The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in Genetics: The Hereditary Material.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5,e4645.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4645
[8] Zhou, M.Y. (2018) Do You Realize Two Basic Questions in Genetic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5, e4396.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4396
[9] Watson, J.D. and Crick, F.H.C. (1953)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Nature, 171, 737-738. https://doi.org/10.1038/171737a0
[10] Baltimore, D., Huang, A.S. and Stampfer, M. (1970) Ribonucleic Acid Synthesis of
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 II. An RNA Polymerase in the Vir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6, 572-576.
https://doi.org/10.1073/pnas.66.2.572
作者 周慕瀛 2018.07.30.
Email fckzmy@sina.com